2020年6月20日,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以下簡稱新修訂《檔案法》)由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并以第47號主席令公布,這標志著我國依法治檔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與1987版《檔案法》(以下簡稱原《檔案法》)相比,新修訂《檔案法》內容更加充實,制度設計更符合檔案工作新的發展需求,如增加了檔案信息化建設和監督檢查兩大章節。其中,檔案利用條款的修訂格外引人注目并呈現諸多亮點。本文試圖從檔案利用權的視角對新修訂《檔案法》檔案利用條款予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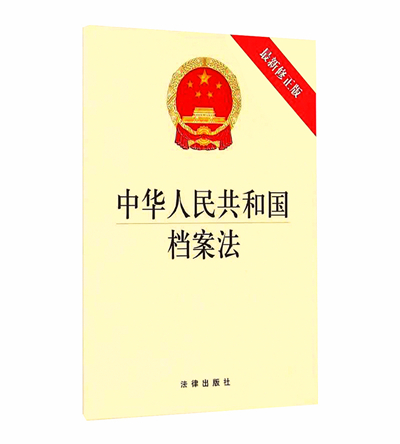
新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封面
總則明示檔案利用權
新修訂《檔案法》第五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武裝力量、政黨、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公民都有保護檔案的義務,享有依法利用檔案的權利。”與原《檔案法》相比,除了依然課以法人和公民保護檔案的義務,還特別增加了他們也“享有依法利用檔案的權利”,將“利用檔案的權利”以宣示性條款列入總則之中。
根據立法技術要求,總則對于分則具有統轄作用,分則的制定必須遵從總則的指導思想。新修訂《檔案法》在總則中明確賦予法人和公民享有依法利用檔案的權利,體現出此次修訂堅持了“服務社會和人民群眾,進一步為檔案開放和利用提供便利條件,增加人民群眾的獲得感”的價值導向。在這一思想的指引下,新修訂《檔案法》涉及檔案利用的條款便有了貫穿始終的原則和精神——檔案利用權。分則各相關條款圍繞“檔案利用權”形成了具有內在聯系的有機整體。與總則對應,分則中進一步細化了利用檔案的權利。新修訂《檔案法》第二十八條和第二十九條分別規定“單位和個人持有合法證明,可以利用已經開放的檔案”。此外,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以及公民,還可以根據經濟建設、國防建設、教學科研和其他工作的需要,“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利用檔案館未開放的檔案以及有關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保存的檔案”。即未開放的檔案,法人和公民也可依法利用。享有利用權利,意味著可以行使權利。不過行使檔案利用權利必須依據合法的方式,如利用開放檔案要有合法證明,查閱不開放檔案要遵照國家有關規定執行。
明晰檔案部門開放檔案的義務
法律是以權利和義務為機制調整人的行為和社會關系。權利和義務是法律的核心內容,二者是對立統一的關系,相互對應、相互依存。“對應”是指任何一項權利都必須伴隨著一個或幾個保證其實現的義務;“依存”則指權利以義務的存在為存在條件,義務以權利的存在為存在條件,缺少任何一方,它方便不再存在。同時,一個社會的權利總量與義務總量相當,如果把權利作為數軸的正側,把義務作為數軸的負側,則權利每前展一個刻度,義務必向相反的方向延展相同的刻度。在利用檔案的法律關系中,利用者是權利主體,它既可以是公民個人,也可以是機關、企業、事業單位或者社會組織;檔案部門則為義務主體,一般為檔案館或檔案室;客體為檔案;法律行為是利用檔案。有關利用的法律規則,就是用來規范與調整利用者與檔案部門在利用檔案的法律行為中產生的權利和義務關系的。公民和法人檔案利用權的實現程度取決于義務主體——檔案部門開放檔案的程度。為了確保檔案利用權的實現,新修訂《檔案法》從以下3個方面進一步細化了檔案館(室)的義務。
1. 縮短檔案控制年限,擴大開放檔案時限范圍
新修訂《檔案法》中,社會各界最為關注的莫過于檔案控制年限的縮減。它要求“縣級以上各級檔案館的檔案,應當自形成之日起滿二十五年向社會開放。經濟、教育、科技、文化等類檔案,可以少于二十五年向社會開放;涉及國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開放的檔案,可以多于二十五年向社會開放”。與原《檔案法》相比,檔案控制年限由30年縮短為25年,擴大了檔案開放的范圍。
檔案控制年限,也稱為檔案封閉期,它的縮短順應了國際檔案界立法的發展趨勢。從世界范圍看,早年多數國家的檔案封閉期為30年。隨著政府管理透明度的日益增強,各國先后出臺《信息自由法》,保障民眾的知情權。為了保持法律體系的一致性,有些國家開始修訂檔案法律,將檔案封閉期由30年縮短為25年或20年,如新西蘭、澳大利亞、南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向以保守著稱的英國。1958年,英國通過《公共檔案法》,規定公眾可以查詢封閉50年以上的檔案。1964年,英國著名政治家哈德羅·威爾遜走上政治舞臺,他認為檔案封閉期50年太久,應該“讓陽光和空氣照進檔案”。在他的敦促下,1967年,英國修訂《公共檔案法》,將封閉期由50年減為30年。進入90年代后,英國發布《開放政府白皮書》,明確提出要在確保公民知情權方面有所作為。1997年,政府決定起草《信息自由法》并最終于2000年通過。依據該法,公眾通過申請即可查閱大量的官方信息,這徹底顛覆了當時執行多年的30年規則。因而,在經過審慎的獨立調查后,英國自2013年始,將政府各部門檔案的控制年限由30年進一步修改為20年。半個世紀以來,英國的檔案封閉期從50年減為30年再減為20年,基本代表了國際檔案界封閉期逐步縮短的演變態勢。
在修訂過程中,既參照了國際慣例,又結合了我國現狀。譬如針對短期內館藏檔案開放鑒定任務劇增、開放檔案鑒定標準尚需細化、專業鑒定人員嚴重匱乏等客觀事實,采用了折中的做法,將控制年限確定為25年,兼顧了前瞻性和現實需要。
2. 拓展開放檔案主體范圍
新修訂《檔案法》另一令人矚目之處是,第十九條規定:“國家鼓勵和支持其他檔案館向社會開放檔案。”將開放檔案的主體由各級綜合檔案館擴展為包含其他檔案館在內的所有檔案館。雖然它只是簡單的一句話,甚至算不上獨立的1個條款,但其影響之大、涉及面之廣不可小覷。其他檔案館包括部門檔案館、企業檔案館和事業單位檔案館,其中最為強勁的一支力量莫過于高校檔案館。
此項規定,從制度層面填補了“開放檔案”的漏洞,邏輯上更加周延。單從理論層面講,檔案館保存的所有檔案終將向社會公開,差別僅在于控制年限的長短。但實際情況是,部門檔案館、企事業單位檔案館長久保存著國家各行業的專業檔案,具有廣泛的文化、科研、教育價值。依據原《檔案法》,開放檔案的行為主體僅限定為國家檔案館,也就是縣級以上各級綜合檔案館和專業檔案館,并未將部門檔案館、企業事業單位檔案館包含在內。換言之,這些館,因法律沒有明確賦予其開放檔案的職責,其形成30年以上的檔案便難以依法公開,導致出現“檔案開放”的巨大漏洞。依據法理,部門檔案館、企業事業檔案館長久保管的檔案,要么向綜合檔案館移交,要么向社會開放。事實上,它們卻很少向綜合檔案館移交,而各級綜合檔案館也沒有足夠的空間和專業隊伍接收這部分檔案,更遑論為社會提供服務。這樣,大量的珍貴檔案價值便難以充分體現,造成了信息資源的閑置與浪費。新修訂《檔案法》從國家層面對現階段我國的狀況作出考量,鼓勵和支持此類檔案館向社會開放檔案。此舉將從制度設計上大幅度地消除檔案開放的“死角”,為國有檔案“物盡其用”提供法律依據。盡管并非強制性規定,只是“鼓勵與支持”,但就高校檔案館的抽樣調查情況看,業界對于開放檔案工作充滿熱情和期待,多表示支持檔案開放,愿意向公眾敞開大門,彰顯檔案價值,發揮檔案作用,在信息社會為檔案行業爭得一席之位。
3. 規范開放檔案的途徑和程序
首先,新修訂《檔案法》強調公布開放檔案目錄的途徑,鼓勵完善利用規則。第二十八條規定:“ 檔案館應當通過其網站或者其他方式定期公布開放檔案的目錄,不斷完善利用規則,創新服務形式,強化服務功能,提高服務水平,積極為檔案的利用創造條件,簡化手續,提供便利。”與原《檔案法》相比,該條款特別明確了公布開放檔案目錄的途徑,即“通過網站和其他方式”。這一修改將有效約束、限制檔案部門濫用權力。早年,受技術條件的制約,一些檔案館“開放檔案”的標志是將編制的開放目錄放置在閱覽室,于是時常有劃控者搬著開放目錄來劃一通,致使1980年代、1990年代部分被利用者復印且在公開發表的文章或史料圖書大量引用過的檔案文獻也被劃進了“控”字序列,還有個別曾經全文公布過的檔案,也未能幸免,一并劃了進去。無獨有偶,更有檔案館規定,利用已經解密的檔案(即開放檔案)要受行政級別限制,要根據局級、正處、副處、一般干部來劃分權限,不能越級利用。新修訂《檔案法》規定,至少將開放目錄放置在網上。一方面,可幫助、引導利用者迅捷獲取檔案存放地點,滿足公眾自由查閱的需要,利于信息的廣泛傳播。另一方面,也可有效地防范檔案部門朝令夕改,隨意劃控。以名人檔案為例,據筆者掌握的信息,不少綜合檔案館、高校檔案館都保管著一定數量的名人檔案,這些人物或為聞名于世的學界泰斗,或是術業有專攻的科技精英,他們的日記、書信、手稿等不僅記錄了個人的成長經歷、學術成就和社會貢獻,還折射出近代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進程,是研究我國文化教育史、社會變遷史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由于以前對檔案開放途徑沒有強制性規定,檔案保管部門與利用者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形成了檔案利用者查檔無門,而檔案館的“故紙堆”卻被“束之高閣”的吊詭怪相。
其次,規范開放檔案的審核程序。新修訂《檔案法》第三十條規定:“館藏檔案的開放審核,由檔案館會同檔案形成單位或者移交單位共同負責。尚未移交進館檔案的開放審核,由檔案形成單位或者保管單位負責,并在移交時附具意見。”該條款科學地界定了政府信息公開和檔案開放鑒定不同的責任主體及其承擔方式,同時將“增量檔案”的開放鑒定進行了分層級處理,將尚未移交進館的檔案鑒定工作前置,交由檔案形成單位或者保管單位負責。這樣,將有效緩解新修訂《檔案法》實施后檔案館“存量檔案”鑒定任務暴增的壓力,可以確保后續工作持續穩定地開展,同時也便于政務信息公開與檔案開放的有序銜接。
最后,鼓勵檔案館開展社會宣傳,發揮檔案館的文化教育功能。2014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的講話中強調,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發揮政策導向作用,使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政策都有利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要用法律來推動核心價值觀建設”。檔案,是凝結中華民族價值取向的一種載體,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檔案館理應成為傳承中華文明、傳播民族文化的重鎮,不能缺位。所以,新修訂《檔案法》特別專列一條,要求“檔案館開發利用館藏檔案,通過開展專題展覽、公益講座、媒體宣傳等活動,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增強文化自信,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檔案館發揮文化教育功能作出具體指引。
劃定檔案利用權利邊界,開啟權利救濟途徑
1. 為檔案利用權利設定邊界
著名法學家張文顯曾指出:“一個人在為實現自己的利益而行使權利時必須設想三方面利益:自己的利益,與自己對應的義務人的利益,權利人義務人之外的第三者即社會的利益。只有這三種利益互不沖突,和諧一致,權利才能真正得以實現。”新修訂《檔案法》在賦予法人和公民利用檔案的權利時,也為該權利的行使設定了邊界,其第二十八條規定“利用檔案涉及知識產權、個人信息的,應當遵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如檔案館保存有大量的名人手稿、書信,日記,利用者若要復制、發表、展覽、攝制、改編、翻譯其中的內容,均不得違反《著作權法》的相關規定。著作權的保護期為作者終生及其死亡后50年。如果作者在世,利用須征得作者的同意;如果作者過世,則須取得權利繼承者的許可。而館藏的婚姻檔案、學籍檔案、病歷檔案等,大多涉及個人隱私,目前國家正在加快《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的立法進度,檔案利用中如何保護第三方權益,也將得以規范。
2. 首開檔案利用權利救濟途徑之先河
法學界有一句經典名言:“無救濟則無權利”,亦即權利的實現需要法律上的救濟來保障。法律意義上的救濟“就是糾正、矯正或改正已發生或業已造成傷害、危害、損失或損害的不當行為……救濟是一種糾正或減輕性質的權利,這種權利在可能的范圍內會矯正由法律關系中他方當事人違反義務行為造成的后果”。檔案利用權利的救濟,則是當法人或公民利用檔案的權利受到侵犯時,他們可以通過適當的方式和渠道,提出申訴與辯解,最終獲得查閱檔案的許可,或者得到合理的裁決。新修訂《檔案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檔案館不按規定開放利用的,單位和個人可以向檔案主管部門投訴,接到投訴的檔案主管部門應當及時調查處理并將處理結果告知投訴人”。首次為檔案利用權利提供救濟途徑。建立救濟機制,可以有效地緩解利用者與檔案部門的矛盾和沖突,保證檔案部門切實履行法定義務,促使利用檔案的權利完成法定權利向實有權利的轉化。
綜上所述,新修訂《檔案法》涉及檔案利用的條款,既有總則中檔案利用權利的宣示,又在分則中對有關主體、客體、行為、結果加以具體規定,同時也對檔案利用權利行使的邊界加以限定,并設置了申訴程序,以及義務主體不依法履行職責要承擔的法律責任,構建了一整套以檔案利用權利為核心,敦促檔案部門切實履行開放檔案的義務、檔案部門違反義務行為后的申訴與追責的制度體系,為保障檔案利用權落到實處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支撐。
參考文獻:
[1]張文顯.法理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國家檔案局政策法規研究司.境外國家和地區檔案法律法規選編[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2017.
[3]王改嬌.從30年到20年:英國加大檔案公開力度大幅縮減檔案封閉期[J].四川檔案,2015(6).
[4]岳斐文.事關開放[J].檔案,2014(1).
[5]張文顯.法理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戴維·M·沃克編.牛津法律大辭典[M].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
作者單位:中國政法大學檔案館